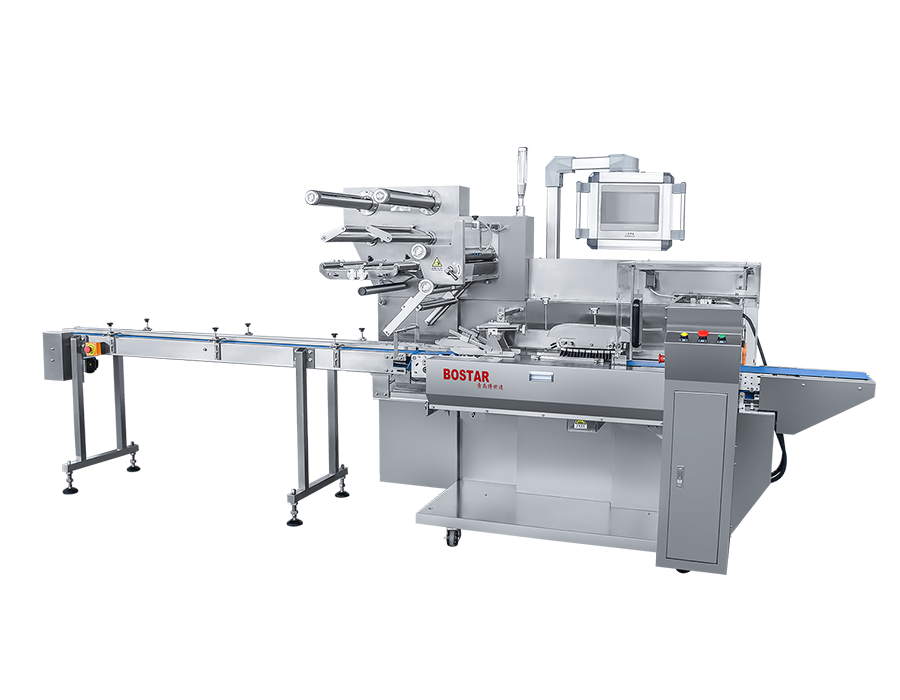人这一辈子,活的便是个眼力见儿。可这眼力,大都都长在了皮面上。看见门口的石狮子神威,就觉得这家是大户;瞅见人穿了身绸缎,就确定他是个富有。
谁又会多想一步,那神威的石狮子,里头说不定是空心的;那光鲜的绸缎底下,许是藏着几块烂疮。
世上的事,就像落在地上的灰,也像陈年的酒,不把它搅动起来,不把它开坛进口,你永久不知道它究竟是呛人的土,仍是迷人的香。
程皓是个刚结业没多久的程序员。跟一切一头扎进这座大城市的年青人相同,他兜里没几个钱,仅有的本钱便是年青,和熬夜加班熬出来的黑眼圈。为了省点房租,他租了市中心一个叫“红星里”的老旧小区的顶楼。房子是老了点,墙皮都泛黄了,但好在廉价,离公司也近。
他的房东陈太太,就住在他楼下。那是一个六十多岁、腿脚不太利索的本地老太太,一个人住。人很和蔼,便是热心得有点过了头。
自从程皓住进来的第一个周末开端,陈太太每周六的晚上七点半,都会雷打不动地,端着一锅热火朝天的老火汤,颤巍巍地爬上楼梯,敲开他的房门。
“小程啊,还在忙啊?阿姨给你煲了汤,补补身子。你们年青人,天天对着电脑,最是耗神。”陈太太笑眯眯地,把一个硕大的砂锅塞到他手里。

程皓一开端,心里是真感谢。觉得这大城市里,还能碰到这么热心肠的房东,是自己的命运。可这汤喝到嘴里,他就觉得不对劲了。那汤,有一股说不出的、很浓重的腥气,像是鱼腥,又像是其他什么。汤里的料,也奇乖僻怪的,除了几块骨头,还有一些黑乎乎的、看不出是啥玩意的“药材”。
他一个北方人,真实喝不惯这种重口味的南派老火汤。可人家老太太一番善意,他也不善意思当面回绝。每次,他都只能硬着头皮,满脸堆笑地收下那锅汤,嘴里说着:“谢谢阿姨,闻着就香,您手工真好!”
等陈太太一走,他就马上把门关上,然后把那锅汤,原封不动地,全都倒进了厨房的下水道里。为了不被发现,他还得把那个沉重的砂锅,里里外外刷得干干净净,一点油花都不留。
第二天,他再毕恭毕敬地把空锅还给陈太太,嘴里还得编着各种瞎话,夸奖那锅他一口都没喝的汤,滋味是多么的鲜美,成效是多么的奇特。
在这个叫“红星里”的老旧居民楼里住了几个月,程皓渐渐觉得,这栋楼里,处处都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乖僻。
楼道里的声控灯,时好时坏,常常得靠大吼一声才干亮起来。墙壁上,处处都是小孩子用蜡笔画的、现已褪了色的涂鸦。空气里,永久充满着一股湿润的霉味,和各家各户飘出来的饭菜味。
最让程皓不自在的,是住在他家对门的那户街坊。那是个默不做声、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整天拉着个脸,像是谁都欠他钱相同。程皓跟他打过几回招待,那男人都仅仅从鼻子里哼一声,算是回应。好几回,程皓在楼道里遇到他,都发现他用一种很乖僻的目光盯着自己。那目光里,有警觉,有烦躁,更难以幻想的是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歹意,如同程皓是什么不祥之物。
小区里的其他白叟,对热心的陈太太,如同也总是敬而远之。程皓好几回看到,陈太太在楼下花园里想跟人搭腔,那些老头老太太们,都找着托言,谦让又疏远地躲开了。他们背面,如同也在议论着什么。
一次,程皓度假,闲着没事,在楼下跟看门房的张大爷下象棋。一来二去,就聊起了楼里的住户。程皓无意中提了一句:“陈太太人真好,每周都给我送汤喝。”
张大爷正准备跳马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抬起头,看了一眼程皓,叹了口气,然后把声响压得低低的,像是在说什么隐秘:“小程啊,陈阿姨她……是个不幸人呐。”
“她仅有的儿子,叫小辉,长得跟你差不多高,也白白净净的。惋惜啊,命欠好,几年前,由于一场意外,走了。听说啊,便是在这个房子里走的。”
张大爷捻着自己的山羊胡子,又神秘兮兮地凑近了一点,弥补了一句:“我跟你说啊,她那个儿子小辉,生前就最喜欢喝她煲的各种老火汤了……小伙子,你跟她儿子年岁差不多,我瞅着啊,她这是把你作为自己儿子了。”
这番话,让程皓心里莫名地有些发毛。他再想起陈太太每次看他时,那过火慈吉祥热切的目光,就觉得后背有点冷冰冰的。但他也没太往心里去,只觉得,这大约便是一个失独白叟,由于怀念过度,而发生的移情作用吧。
一开端,仅仅下水的时分,水流会打着旋,下去得很慢。后来,发展到洗个碗,水槽里都会积起半池子的污水,得等上好半响,才干渐渐地漏下去。
他自己心里清楚,这多半是跟自己长时间倾倒那些油腻的汤水有联系。他心里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哪天完全堵死了,被房东发现,那就为难了。他跑到超市,买了好几瓶听说作用很神的强力管道疏通剂,一股脑地全都倒了下去。冲鼻的化学药剂滋味,在屋子里充满了好几天,可阻塞的状况,也仅仅略微好转了一点点。

每周六的晚上,依旧是程皓最“折磨”的日子。陈太太仍是会雷打不动地,在七点半按时敲响他的房门,端来那锅腥味扑鼻的汤。
她的目光,越来越慈祥,看得程皓浑身不自在。她乃至开端不再叫他“小程”,而是直接叫他“小辉”。
她还会拉着程皓的手,絮絮不休地想念一些他完全听不懂的、关于“小辉”小时分的小事。比方小辉小时分最喜欢玩什么玩具,第一次考一百分是何时,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是啥样子……
程皓越来越害怕了。他觉得,陈太太的精力问题,或许比他幻想的要严峻得多。他不敢辩驳,也不敢纠正,只能生硬地笑着,嗯嗯啊啊地应付着。
他一边胆战心惊地应付着陈太太,一边愈加小心谨慎地处理那些汤。他不敢再把汤里的那些骨头和看不出名堂的“药渣”直接倒进水槽。他每次都会先用漏勺,把汤里的固体残渣全都捞出来,仔细心细地用塑料袋装好,打上死结,然后趁着夜深人静,偷偷地带到楼下那个最大的公共垃圾桶里丢掉。他只把那些油腻的汤水,倒进自家厨房的水槽。
程皓睡过了头,急急忙忙地跑到厨房洗漱。他一翻开水龙头,水槽里的水就敏捷积了起来,并且,一股夹杂着食物糜烂和油污酸败的恶臭,从下水道的管口,汩汩地返了上来。水槽完全停工了。
程皓真实是没方法了。他硬着头皮,给小区的物业打了个电话,恳求他们派一个专业的疏通工人来修补。
就在他焦急地等候工人上门的时分,门,又被敲响了。程皓一惊,心想,今日才周三,陈太太怎样来了?
他翻开门,果然是陈太太。她一手端着那锅了解的砂锅,另一只手,还拎着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包。
“小辉啊,妈看你这几天如同脸色不太好,是不是作业太累了,没歇息好?”陈太太一脸关心地把砂锅和纸包都塞到了程皓手里。
“这是我今日特意去老街那家老药铺,给你抓的补药。你把它加到汤里,一同喝了,对身体好,能补气血。”
程皓垂头看了一眼手里的那个牛皮纸包。纸包不大,但沉甸甸的。他翻开看了一眼,里边是一些黑褐色的、晒干了的、看不出是什么植物的根茎和叶子。一股冲鼻的、混合着泥土和腐朽植物的奇怪气味,扑面而来,熏得他差点打了个喷嚏。
送走了陈太太,程皓看着手里的这包“补药”,心里犯起了嘀咕。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下午,他抽暇,偷偷地从那包药里,拿出了一小撮药渣,用纸巾包好,揣在兜里,去了小区邻近一家挂着“百年老店”牌子的中药铺。
药铺里,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药师,正坐在柜台后打盹。程皓把那撮药渣递过去,谦让地问:“老师傅,您能帮我看看,这是什么药材吗?”
老药师接过药渣,把它放在鼻子底下,细心地闻了闻,又用两根干瘦的手指,捻起一点,放在指尖搓了搓。
遽然,老药师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像是碰到了什么脏东西相同,猛地把手里的药渣扔回纸巾上,然后用力地把纸巾推还给程皓,连连摆手。

“不知道!这东西咱们店里没有,也历来不敢有!”老药师的口气,带着一种显着的嫌恶和一丝惊骇,“小伙子,我劝你一句,这可不是什么正派的补药,你可千万别乱吃!会出事的!”
老药师讳莫如深,又不愿多说的表情,像一把小锤子,在程皓的心上,重重地敲了一下。
老药师那番话,和那副见了鬼相同的表情,让程皓心里那根一向紧绷着的弦,完全绷紧了。
他回到自己那间小小的出租屋,只觉得屋子里处处都透着一股阴冷的气味。他越想越不对劲。
他想起了陈太太那越来越乖僻的行为,和她口中那个越来越频频的姓名,“小辉”。
一种巨大的、不祥的预见,像一张无形的网,瞬间笼罩了他。他感觉自己如同掉进了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旋涡里。
他翻开电脑,开端张狂地在网上查找。他输入了各种关键词:“老火汤 腥味”、“民间偏方 补药”、“特殊气味 草药”……他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想找什么,他仅仅被一种天性的惊骇唆使着。
查找成果形形色色,有些乃至看得他有些反胃。但其间一些关于土方、巫蛊、乃至是一些现已被明令禁止的、用来处理尸身的民间方法的描绘,看得他手脚冰凉,毛骨悚然。
工人是个经历比较丰富的中年师傅,姓王。王师傅拎着一个大工具箱,一进门就皱起了眉头:“小伙子,你这屋里什么味儿啊?怎样这么臭?”
程皓为难地笑了笑,把他引到厨房。王师傅看了看那被堵得死死的水槽,二话不说,就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条长长的、像绷簧相同的疏通器,捅进了下水道里。
他捅了半响,额头上都见了汗,那疏通器却像是撞在了一堵墙上,怎样也捅不进去。
王师傅直动身,擦了把汗,摇了摇头,下了最终的定论:“不可。你这下面,是主管道的U型存水弯那里,被什么又多又硬的东西,给完全堵死了。惯例方法没用,有必要得把这段水管拆开,把里边的东西掏出来才行。”
王师傅从他的大工具箱里,拿出了一把巨大的活动扳手,和一把小型的金属切割器。他蹲下身,钻进水槽下面的橱柜里,开端对着那节堵得最死的U型管道,下起了手。
尖锐的金属冲突声,在安静的屋子里响起,像指甲划过玻璃,听得程皓心里一阵阵发紧。他严重地站在一旁,手心里满是汗,眼睛死死地盯着王师傅的动作。
衔接管道的几个巨大螺丝,由于年久失修,早已锈迹斑斑。王师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涨得满脸通红,才总算把它们一个个地拧松了。

就在管道与主管道别离的那一瞬间,一股比之前浓郁百倍的、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恶臭,像一颗炸弹相同,瞬间从管道的断口处喷涌而出。那是一种混合着腐肉、油脂酸败和化学药剂的、令人作呕到极点的气味。
“!”王师傅被这股恶臭熏得猛地往后一仰,连连干呕。程皓也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捂住口鼻,踉跄着后退了好几步。
王师傅缓了好一阵,才从兜里掏出一个发黄的口罩戴上。他拿起那节看起来反常沉重的U-型管,把它倒转过来,往地上预先铺好的几张旧报纸上,使劲地磕了几下。
一些黑色的、油腻的、现已凝结成膏状的淤泥,和一些分辩不出是啥东西的、沤烂了的食物残渣,黏糊糊地掉了出来。
但是,管道里,如同还有啥东西,像被水泥灌注了相同,卡得死死的,底子倒不出来。
王师傅皱紧了眉头,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根长长的、头部带钩的铁丝,嘟囔了一句:“妈的,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堵得这么死。”
他把那根长铁钩,伸进了黑洞洞的管道里,使劲地、来回地搅动着,钩着,往外掏。
一个被黑色的油污和黏糊糊的淤泥,包裹得结结实实的、硬邦邦的东西,被他从管道里钩了出来。
让他瞬间如遭雷击,头皮发麻,浑身上下一切的血液,如同都在这一刻,被冻成了冰!
上一篇:城市跑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