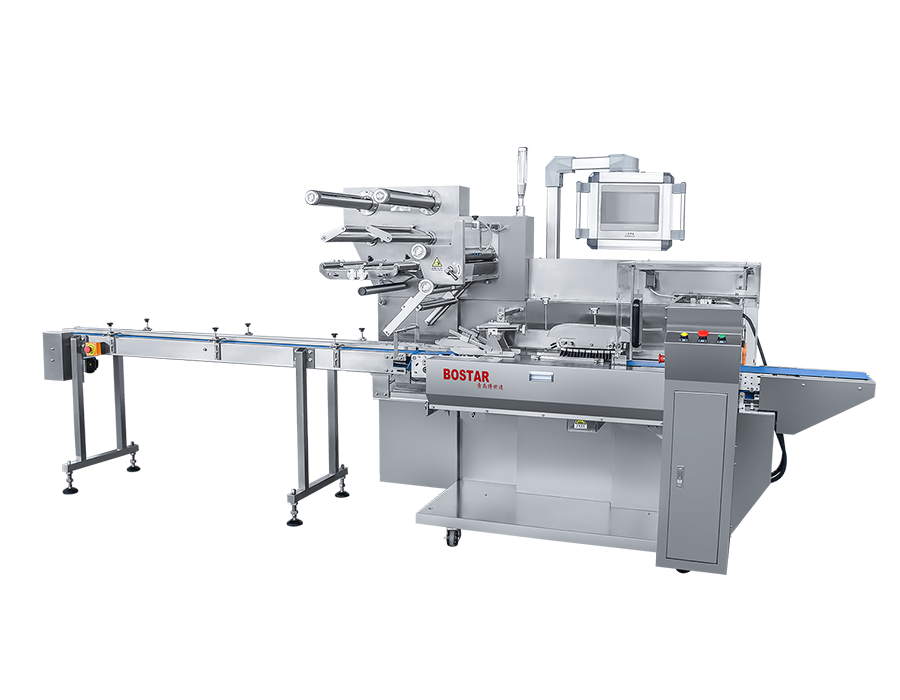今世言论场中,1929年希伯伦事情常被简化为阿拉伯人仇犹赋性的注脚,用以证明即便没有196年占据与1948年大灾难(Nakba),阿拉伯人仍然会杀戮犹太人。这种叙事将杂乱前史压缩成种族宿命的图解,固化着施暴者—受害者的二元敌对。但当镜头推近前史的褶皱,这场残杀实则是多年敌对淤积的火山喷射,其岩浆源自更深层的社会政治变迁。
奥斯曼帝国时期,巴勒斯坦社会曾欢迎被西班牙驱赶的塞法迪犹太人。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种联系在外部强权干涉下继续恶化。要害转折点始于1882年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人不再寻求维护,而是索要主权。这一底子改变彻底重构了巴勒斯坦的政治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192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内部对犹太人的认知仍存在细微差别。在阿拉伯语白话与书面语中,阿拉伯犹太人(指长时间融入中东文明的塞法迪社群)、犹太复国主义者(指带着番邦风俗的东欧移民)与斯科纳人(指敌对复国主义的极点正统派)等词汇仍有区别。采法特的科恩宗族、阿弗里亚特宗族,希伯伦的卡斯特尔宗族、阿布什迪德宗族与卡皮洛托宗族,在暴动中曾向阿拉伯街坊呼喊咱们是兄弟,却未能幸免。
但是,这些区别在暴力高潮中的确瓦解了。暴动提醒了一个严酷实际:对阿拉伯社会而言,犹太社群内部的政治不合、宗教光谱与代际差异已失去含义。不管陈旧社群仍是新移民,尘俗派仍是正统派,左翼仍是右翼,一切团体同享三个中心信仰——犹太民族性、回归权与在巴勒斯坦树立犹太国家。在1920年代末的政治氛围下,这些共性足以掩盖一切不合,使持此理念的犹太人在阿拉伯人眼中构成威胁性的全体。阿拉伯突击者自认并非残杀街坊,而是在敌对妄图夺占其家乡的敌人。
1929年8月的血色暴力中,线;的标签杂乱。遇害者中既有突击者,也有被阿拉伯街坊躲藏的犹太人;施暴阵营里亦存在冒死解救犹太老翁的青年。英国官方组成的肖氏调查团(Shaw Commission)得出的定论,已被今世叙事故意淡化:突击并非预谋,其终究的原因在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政治期望受挫与经济远景暗淡而对犹太人发生的歹意,而直接导火线是哭墙的一系列寻衅事情。
调查团清晰将事情定性为政治抵触而非种族仇杀。其时的控制者英国确定,暴力根植于政治经济挫折,而非律法对异教徒的敌视。这一判别与简化叙事构成尖锐敌对。
西墙(哭墙)争端是压垮骆驼的终究一根稻草。在奥斯曼与英国初期控制下,西墙处于奇妙的同享状况:犹太人有权祈求,但不得带着任何暗示主权或将其变为犹太礼堂的物品(如长凳、屏风、国旗)。1928年赎罪日前夕,这种平衡开端决裂。1929年8月,泽夫·贾博廷斯基领导的急进修正主义青年运动贝塔举行了一场寻衅性,升起犹太复国主义旗号,高唱《期望》歌。这并非宗教祭奠,而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性宣告。
温和派犹太复国主义首领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后遭暗算)揭露斥责此举为莽撞鼓动,旨在故意激怒阿拉伯国际。事态随后失控,鼓动性布道与流言四起,整个巴勒斯坦好像火药桶。
在这场污浊的暴力潮中,存在被故意忘记的合作瞬间:布哈拉犹太区的店东西蒙将受伤的阿拉伯少年藏入地窖;阿拉伯老妇米娜顶着枪声维护犹太母女穿越冷巷。这些碎片化的亮光未能载入任何一方的英豪谱系——敌对的编年史家更热心记载敌人的残酷。在代尔亚辛村,1929年曾突击犹太社区的阿拉伯人不会想到,二十年后这儿将成为犹太装备报复性残杀的现场,并被写入国际新闻头条。前史复仇的循环在此埋下伏笔。
暴动后的媒体出现,暴露了回忆怎么被政治化。《国土报》在1929年9月2日刊文否定犹太人的任何暴力行为,宣称非吾纵火/非吾嗜血抢掠。但就在两周前的8月18日,同一家报纸曾剧烈斥责两边鼓动者,且修改彻底知晓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对阿拉伯人施行私刑、在辛基斯杀戮阿拉伯白叟全家的现实。这种选择性叙事,为读者供给了非黑即白的品德图景,服务于伊休夫(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自我形象建构。
阿拉伯方面的叙事相同简化。两边都将对方描绘成永久的加害者,将本身塑造成朴实的受害者。这种互为镜像的叙事战略,在代际更迭中不断自我强化,终究固化为不行谐和的团体回忆。
史学家希勒尔·科恩在《阿以抵触元年》中提醒要害洞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只点着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巴勒斯坦人的抵挡反过来也铸造了犹太人的联合认同。两者在敌对中彼此形塑。
更深层的前史线世纪。当欧洲实力浸透奥斯曼帝国,犹太人与基督徒寻求西方领事维护时,传统中维护经文之民的职责被从头审视。1834年的法律文书记载闪现,当地宗教学者已提出:若受维护者转为外来实力代理人,维护契约主动失效。这种法理争论,为日后的暴力供给了宗教合法性外衣。
1882年第一次阿利亚期间,文明抵触已在雅法码头闪现:坚持欧式穿戴的俄国移民回绝阿拉伯贴面礼,被保守长老视为高傲;安息日点着煤油灯的行为,更被视作亵渎。塞法迪犹太人夹在中心,既被东欧同胞斥为东方落后分子,又被阿拉伯街坊置疑与外来者共谋。
回望希伯伦惨案,不应再视其为种族天分的展柜,而应了解其为前史混凝土前期进入的裂缝。一切未解的张力——殖民浸透、民族自决诉求、文明磕碰、经济焦虑——都在其间奔涌成形。暴力历来不是赋性使然,而是政治失利、团体惊骇与前史积怨的化合反应。当简化叙事将职责归于陈旧仇视时,它恰恰遮盖了真实需求审视的前史症结:平和怎么或许,当一方的民族完成树立在另一方政治失望之上?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近百年前裂开的那道缝隙中,至今未能愈合。
首要需求正名:应该是1929年希伯伦抵触和1920年耶路撒冷抵触,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大残杀”含糊了职责鸿沟,变成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全责。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购地赶农断人生计,不会有阿拉伯人群情激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