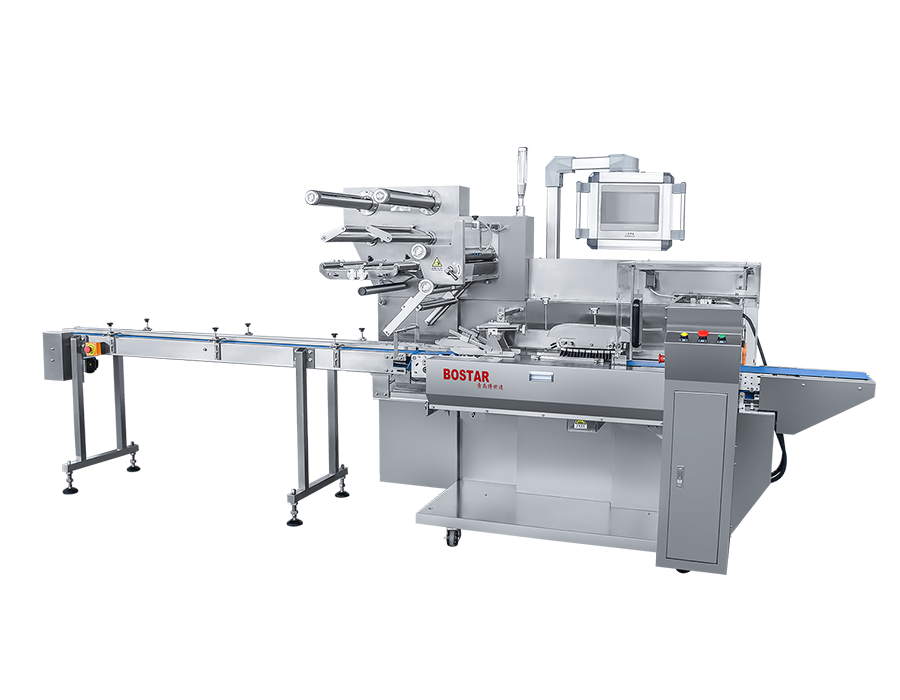轿车沿京新高速向蒙北草原行进,过了张家口界后,风里的气味便被内蒙的广阔渗透——先是呼伦贝尔的青草甜香,再是额尔古纳的湿地水汽,最终裹着阿尔山的松针凉、巴丹吉林的沙砾味与手把肉的醇香,扑进沾着奶豆腐碎屑的车窗。这不是攻略里“天苍苍野茫茫”的空泛标签,是草原晨雾中晃动的马影,是湿地正午阳光下的水鸟,是阿尔山暮色里的火山岩,是沙漠星夜下的梭梭林,更是这些景象背面,看护者掌心的温度。
十日的穿行像打开一卷浸过呼伦河水的油布,每一页都写满人与内蒙山水的相守暗码:一页是草原的青,印着牧民的蹄痕;一页是湿地的绿,刻着巡护员的足痕;一页是林海的深,凝着护林员的刀痕;一页是沙漠的金,藏着治沙人的锄痕。
呼伦贝尔草原(中心莫日格勒河+金帐汗部落外围):晨雾中的套马杆与草原看护
呼伦贝尔的晨雾还没漫过莫日格勒河的河湾,牧民巴图的套马杆现已指向了远方的马群。“要趁日出前赶马,晨雾里蚊虫少,马群静,这草原是内蒙的魂,得细护。”他的藏青色蒙古袍沾着草露,羊皮郛里揣着本磨毛边的《草原巡护日志》,那是他跟着阿爸守在这片草原的第三十二个年初——从帮阿爸给小小羊喂奶,到成为“草原卫兵”,他的手掌早被套马杆磨出了厚茧,指甲缝里永久嵌着洗不净的草色汁液,连笑起来眼角的纹理都像草原的褶皱。
咱们跟着巴图往莫日格勒河走,脚下的青草被雾打湿后沾着露珠,每一步都踩着“沙沙”的轻响。空气里混着酥油的醇香与马奶酒的微烈,远处的蒙古包在雾中只剩含糊的白顶,风卷着雾絮从河湾钻出来,打在脸上带着草原的微凉。巴图遽然停在一片芨芨草旁,套马杆悄悄拨开草叶:“这草是马群的口粮,2021年大旱时枯死了多半,咱们跟着技术员种耐旱的冰草,又从河里引水浇地,花了两个月才让草从头长起来。”他指着远处的铁丝网:“那是2020年修的生态围栏,把草原分成了六块轮牧,曾经马群乱啃,草都长不齐,现在轮着歇地,草比上一年高了半尺。”
走到莫日格勒河的“九曲回肠”观景台时,晨雾里遽然传来马群的嘶鸣声,巴图翻开日志,指着2019年的相片:“那时飓风‘利奇马’外围带来暴雨,河湾冲垮了牧民的草垛,咱们用毡布挡水,又帮着搬运牛羊,守了三天三夜才保住牧群。”他指着不远处的“饮水槽”:“那是2018年修的,曾经马群要跑十几里地到河滨喝水,现在每个围栏里都有槽,既便利又维护了河边的草。”晨光渐盛时,向阳从雾缝里探出面,金光照在河面上,瞬间铺开一片碎金,风一吹,雾絮散开,显露莫日格勒河“天下榜首曲水”的全貌——河水像银色的绸带缠绕在青绿色的草原上,远处的马群披着金光奔驰,露珠溅在脚上,带着青草的清甜。
从呼伦贝尔驱车向东行两小时,额尔古纳湿地的阳光已透过芦苇丛,在湿地上投下跳动的光斑。湿地巡护员萨仁的望远镜现已对准了远处的白鹤。“要趁正午观鸟,日头足时鸟群活泼,看得清,这湿地是内蒙的肾,得细护。”她的天蓝色工装沾着泥点,帆布包里揣着本卷边的《湿地观测日志》,那是她看护这片“亚洲榜首湿地”的第十七个年初——她的父亲是湿地榜首代巡护员,教她“辨鸟听声、识草看叶”的法子,现在她守着父亲传下的望远镜,成了湿地的“活鸟谱”。
咱们跟着萨仁往根河河谷走,木栈道的木板被晒得微暖,每一步都踩着“笃笃”的轻响。空气里混着芦苇的幽香与水苔的湿味,远处的根河像一条碧绿的绸带弯曲在湿地中,偶然有白鹤的长鸣声从芦苇丛里传出来,混着望远镜的“咔嗒”调焦声。萨仁遽然停在一处观鸟台旁,手指着水面的水葱:“这草能净化水质,2022年汛期冲来的废物缠在草上,咱们带着志愿者划着独木舟收拾,一天下来浑身都泡皱了,花了五天才清洁净。”她指着栈道旁的标识牌:“那是2019年立的,曾经有游客摘湿地的花,现在都知道这些是维护植物,没人乱碰了。”
走到湿地的制高点时,正午的风掀起萨仁的日志本,阳光透过镜片洒在泛黄的纸页上,上面记取每种鸟类的迁徙时刻与筑巢方位。“这额尔古纳湿地是留鸟的驿站,每年春秋两季,白鹤、大雁都会在这歇脚,”萨仁摩挲着望远镜的金属镜筒,“那是2017年禽流感时留下的记载,其时咱们给湿地消毒,又在周边设了观测点,守了一个月才保证留鸟安全。”她从兜里掏出一片晾干的碱蓬草,是从湿地边际采的,叶片带着淡淡的红晕:“这草秋天会变红,整片湿地像铺了红地毯,曾经牧民把它晾干了当柴烧,现在咱们都护着,让它给留鸟当藏身的当地。”

从额尔古纳驱车向西行四小时,阿尔山的暮色已给火山岩镀上了层金边,林海护林员老秦的砍刀现已砍断了一丛杂木。“要趁日落前修枝,暮色里木茬不扎手,砍得齐,这林海火山是内蒙的骨,得细护。”他的深绿色工装沾着松脂,帆布包里揣着本《林海巡护日志》,那是他看护这片“火山博物馆”的第四十个年初——他是林区的原住民,小时候跟着爷爷巡山,现在守着爷爷传下的砍刀,成了林海的“活地图”。
咱们跟着老秦往天池走,山间的石阶被落日染成橙红,每一步都踩着“笃笃”的响。空气里混着落叶松的幽香与火山岩的土腥,远处的天池像一块蓝宝石嵌在群山间,三潭峡的溪流从火山岩间流过,偶然有松鼠的吱吱声从树丛里传出来,混着砍刀的“咔嚓”声。老秦遽然停在一棵落叶松旁,砍刀悄悄砍去缠在树干上的藤蔓:“这树有五十年了,2021年飓风‘焰火’吹断的藤蔓缠得它快枯死,咱们用剪刀一点点剪,花了两天才清洗收拾洁净。”他指着路旁边的火山岩:“这是玄武岩,是火山喷射构成的,曾经有游客搬回去当纪念品,咱们立了‘岩怕搬’的牌子,现在石头都好好的。”
走到天池的观景台时,暮色的风掀起老秦的日志本,落日的余晖洒在天池水面上,泛着粼粼波光。“这阿尔山天池是火山口湖,有三百多万年了,水从来没干过,”老秦摩挲着观景台的栏杆,“那是2018年防火期留下的记载,其时有游客乱扔烟头引发小火灾,咱们带着队员砍防火带,守了两天才熄灭,现在每个进口都有防火查看。”他指着不远处的“引水渠”:“那是老法子,用火山岩砌的渠,把山泉水引到巡护站,既健壮又不损坏环境,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手工。”
从阿尔山驱车向南行六小时,巴丹吉林沙漠的星子已缀满必鲁图峰的上空。治沙人王建军的铁锹现已了沙地里,正往坑里栽梭梭苗。“要趁星夜栽苗,露珠润着沙子不烫,苗易活,这沙漠是内蒙的魄,得细护。”他的土黄色工装沾着沙砾,帆布包里揣着本《治沙日志》,那是他看护这片“沙漠珠峰”的第二十八个年初——他是治沙人的子孙,小时候跟着父亲种梭梭,现在守着父亲传下的铁锹,成了沙漠的“播绿人”。
咱们跟着王建军往沙漠绿地走,脚下的沙子被月光照得发亮,每一步都陷下去半尺,踩着“咯吱”的轻响。空气里混着沙枣的甜香与梭梭的淡味,远处的必鲁图峰在星夜中像一座黑色的巨塔,绿地的灯光在沙漠中像点点星光,偶然有沙狐的叫声从沙丘后传出来,混着铁锹的“沙沙”铲沙声。王建军遽然停在一片梭梭林旁,手指着长势喜人的麦苗:“这梭梭是2020年种的,曾经这片满是流动沙丘,咱们用草方格固沙,又浇了从绿地引来的水,现在苗成活率达到了多半。”他指着远处的草方格:“那是2019年扎的,用麦草扎成正方形,能挡住流沙,这是治沙人的保命法子。”
走到绿地的蓄水池旁时,星夜的风掀起王建军的日志本,月光洒在沙地上,像铺了一地银霜。“这巴丹吉林沙漠看着荒芜,其实有一百多个绿地,是沙漠里的生命线,”王建军摩挲着铁锹的木柄,“那是2015年大旱时留下的记载,其时蓄水池快干了,咱们从几十公里外拉水,又给梭梭苗浇生根水,守了一个月才保住这片林。”他指着不远处的沙枣树:“那是老祖宗种的,树龄有上百年了,结的沙枣又甜又顶饿,现在咱们新种了两百多棵,让绿地渐渐的变大。”
星夜渐深时,萤火虫从绿地的草丛里飞出来,点点微光绕着梭梭苗转,像撒了把碎星。王建军从兜里掏出一把晾干的沙枣,是从老树上摘的,果肉带着嚼劲:“这沙枣能当零食,曾经治沙人饿了就靠它,给你藏着,记取沙漠的甜。”他又拿出一把旧铁锹,锹头是钢制的,现已磨得很薄,手柄是老榆木:“这铁锹陪了我二十年,挖过最硬的沙层,也栽过最小的苗,巴丹吉林的每一座沙丘我都熟。”我捏着枯燥的沙枣,指尖还能触到沙砾的粗糙,遽然懂了巴丹吉林沙漠的美——不是“沙漠珠峰”的噱头,是沙的金、绿的嫩、王建军的守,是内蒙把最坚韧的岁月,藏在了星夜的沙地里。脱离时,他还在给新栽的梭梭苗洒水,铁锹靠在蓄水池旁,风掠过沙漠的“呼呼”声,混着沙枣林的轻响,成了夜色里最动听的节奏。